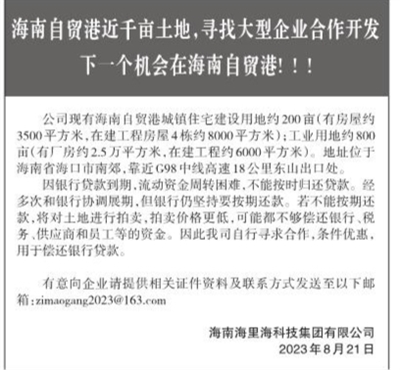【資料圖】
【資料圖】
作為紀錄片,《巢》很難望文生義。看完片子,我還想了想片名到底指什么。導演很可能是指電影中一家三口住的那套一室戶房子。兒子已經成年了,三口人住一室戶當然很局促。但局促和局促還有不同。有些局促會讓人產生生存論疑問,片中的人物雖然時時探討人活著有什么意義,但從來沒有上升到生存論層面。這家人的痛苦主要是圍繞著兒子無窮無盡的日常挫敗展開的,住房問題并不是焦點。看電影的時候,這個年輕人讓我想到文學史上有一種典型的多余人角色:觀念過剩,行動力弱,道德麻痹,完全以自我為中心。但事后想起來,這家人應對挫敗的方式很實在,家庭、親戚、教會和政府也形成了一個社會學意義上的保障機制,他們吵吵鬧鬧甚至尋死的時候,都給我生機勃勃的感覺,就像一窩鳥似的。這當然也是巢。
我很早認識導演秦瀟越,因此幾年前看過一部分素材,但還是對這部電影的完成度感到驚訝。當我說紀錄片的完成度時,主要不是說電影的結構和情節,而是說它的密度。去年看了不少1990年代上海的紀錄片,很多是上海廣播電視臺紀錄片中心的作品,因此有著類似的質地:粗糙而密實,沒有明確主題。這些紀錄片并沒有任何過時的感覺,主要不是因為它們講的故事,而是因為講故事的方式。這些為電視臺而不是電影院制作的紀錄片保留了數不清的物質和情感細節。到底當時的導演們意識到無限度貼近拍攝對象和高密度的鏡頭語言是一種獨特的風格,還是他們沒有其他技術選擇,只能忍受那晃動粗糙的畫風,今天看來已不重要。因為時間做出了自己的選擇。這種選擇比觀眾和獎項都要可靠。
秦瀟越和這一代導演差了兩代人。《巢》是她的第一部長片,風格卻很相近。雖然被評為今年First青年影展最佳紀錄片,但在今天的紀錄片市場上,《巢》這種風格絕非主流。
前一段時間,因為討論到偏好與風險的關系,和兒子一起看了紀錄片《徒手攀巖》。這部片子的敘事遵循美式紀錄片常見的情節模式:懸念-困難-克服,拍得很工整。雖然題材驚險,但展示了導演和拍攝團隊的控制力。特別是在主題的闡釋方面,有時我覺得控制得有點過頭。這當然是見仁見智的事。如何理解紀錄片的主題,本來就很困擾人。
這里有個基本的悖論:電影敘事通常是一種隱喻,但紀錄片除外。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現代啟示錄》是一部象征主義電影,但關于這部電影拍攝過程的紀錄片非常平實,除了讓人知道拍攝過程中的種種困難,并沒有想傳達其他意圖。當然,可以說這類紀錄片作為劇情片的副產品,某種程度上分享了劇情片制造的話題效應,并因此和它的主題聯系在一起。但在我看來,要賦予紀錄片過于明確的主題,總是令人尷尬的事,實際上制片過程也很困難。
我參加過一些主題先行的紀錄短片項目,對此深有感觸。現在不少紀錄片導演靠拍這類短片為生,通常是來自媒體的訂單。他們往往還有更個人化的項目,準備拍成長片,需要用短片中掙的錢維持。這肯定不算是一個好的或說可持續的模式,但現實中的確沒有其他可能的模式。矛盾的是,導演制作長片的手法和制作短片的手法沒有什么區別。他們也總是孜孜于為自己的電影尋找合適的主題,如果找不到,就非常困擾。
主題不止是紀錄片導演個人的困擾,對發行方也是一個問題。歸根結底,這是電影市場也就是觀眾的偏好決定的。圍繞一個主題制造懸念和困難,再去解決困難,揭開懸念,商業電影遵循這種情節模式當然有道理。《碟中諜》和《諜影重重》之所以能拍許多無聊的續集,證明這種情節模式雖然俗套,卻能最大發揮商業電影的市場潛力。這些年紀錄片制片人拼命想爭取的發行市場,正是商業電影的溢出效應。從商業電影市場里溢出來的當然不止票房,還有觀眾的偏好——稱之為習慣也許更合適一些,因為習慣其實是偏好與環境互動的產物。新的習慣需要不同的環境。
要求紀錄片遵循這類商業電影的模式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制片方式完全不同。只有在不同的環境(當然包括一個小但真實存在的市場)中,主題和風格這類困擾著導演的問題,才會有和目前不同的解決思路。觀眾當然會向紀錄片導演提出高要求,比如我說的密度,但這種要求必然不會以某一類商業電影的標準為標準。不少紀錄片導演的確希望在商業電影市場中獲得成功。這樣他們就不得不面對商業電影的發行商和觀眾。我確信這是個不可能的任務,但仍然會有人去嘗試,原因不是別的,只是因為改變環境比改變自己要難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