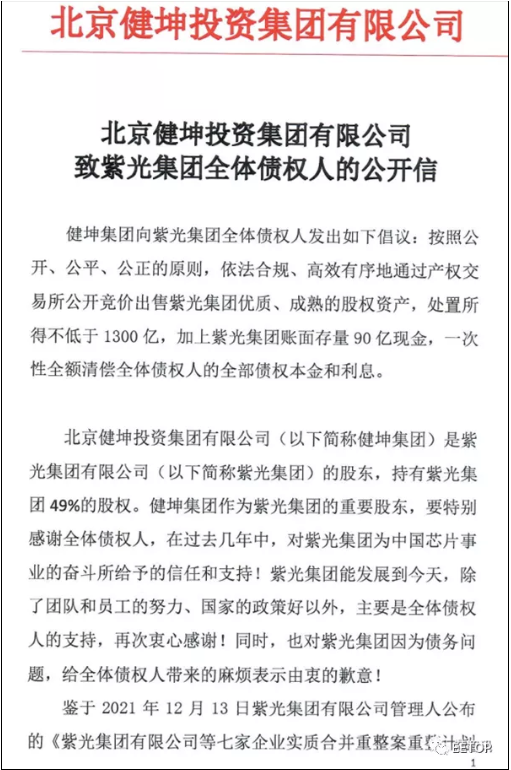能源效率提升是當前能源發展現實條件下實現高質量碳達峰的重要手段,也是未來實現碳中和的重要途徑之一。
傳統能源結構下占據主體的化石能源屬于典型的可枯竭性自然資源,如何利用有限的能源資源支撐經濟社會發展是全社會共同關注的重要問題。因此,傳統能源效率側重于描述經濟產值與能源消費量之間的多種關系。
隨著我國未來能源結構顛覆性轉變、能源成本重新定義、環境成本日益受關注、脫碳效果要求更加嚴格,傳統的主要關注能源消費總量(標準煤)和經濟產值的能源效率評價方法已經不能滿足我國“雙碳”(即“碳達峰、碳中和”)總體目標下的能源效率評價需求。如何在新的視角下界定能源效率和如何提升能源效率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區分新能源與化石能源商品屬性
能效考量體系要有新內涵
“雙碳”目標驅動下以風光為主的新能源將逐步代替傳統的化石能源,而新能源與傳統化石能源的商品屬性具有顯著差異,包括可獲取性、獲取成本、能源密度、碳排放量等。
在未來近乎無限的風光等可再生資源占據主導地位的系統中,我國能源經濟應該更加關注能源全生命周期內的能源消費量、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及能源相關設備生產過程能耗等。
在此背景下,將“能源環境效率”與傳統關注的“能源物理效率”和“能源經濟效率”一同放入“雙碳”能源效率的綜合考量體系當中,更加有助于科學完整地評價能源生產和利用的效率,也更加有助于推動我國“雙碳”目標的實現。
著眼產業實情
因地制宜提升城市能效
能源經濟效率提升以產業升級和產業結構調整為主,不同發展階段的城市有不同策略。
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自2012年以來累計降低24.6%,相當于減少能源消費12.7億噸標準煤。但從2020年總體能源效率來看,我國單位GDP能耗仍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發達國家的3倍,能效提升仍存在較大空間。
大量研究指出,這是由于我國產業結構與OECD國家存在差距的原因。然而產業結構調整幅度與能源效率提升之間并非完全正相關關系,如何區分產業結構能效與產業鏈占比能效、因地制宜提升城市能源效率,是新時期能源指標需要思考的問題。
如一部分工業發展階段較為落后的城市應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重點關注結構能效。部分城市工業化進程落后于我國平均水平,存在第二產業落后產能過剩以及第三產業發展基礎薄弱等綜合產業發展困難。這類城市的能效提升過程應該著重關注城市整體產業結構能效,積極承接區域間產業轉移,有效借鑒發展領先地區“退二進三”和“騰籠換鳥”經驗,推動地區資本有低效率向高效率移動,產業結構由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過渡。此外,勇于為新經濟、新業態和新動能在政策和制度上創新突破也是這類城市實現跳躍式經濟結構發展的機會,從而大幅提升區域整體能效水平。
另一部分城市適合通過發揮既有產業優勢、推動產業升級、向上游改善產業鏈所處位置,重點關注產業鏈能效。這類城市承擔了我國各類制造業基地和中心的重任,能源消費較高的同時也承擔起了重要國際產業鏈支撐、國家基礎行業領頭人和區域實體經濟基礎的重要角色。這類城市切忌通過產業結構大幅度調整提升能效,明確產業調整“重質量”而非“重幅度”,重“產業鏈所處環節結構”而非“城市整體產業結構”,重同行業跨國家、跨城市橫向對比而非同城市內跨行業能效水平對比。把握自身優勢產業,通過科技創新促進產業向知識技術密集型環節(上游)拓展升級是這類城市向產業要能效的重要途徑。
強化能源綜合利用
消除跨網互濟壁壘
從重點高耗能行業來看,我國單一環節的能源利用效率,例如發電效率、電網綜合線損率、電池轉換效率等基本處于世界領先水平。光伏發電多次刷新電池轉換效率世界紀錄,中國今年建設全球首座20萬千瓦高溫氣冷堆發電效率可以達到40%以上。
但與單一環節能源效率領先的現狀不同,我國系統能效水平目前仍處于較為落后的階段,這主要是受不同能源品種協同壁壘較大、跨網互濟深度有限所致。
一方面通過加強綜合能源系統建設和應用著力解決能源系統協同能力弱的問題,從而提升系統能效。
以2020年源端新能源發電情況為例,全國風電量和光伏電量平均利用率已經高達97%和98%,但5.3億千瓦的風電和光伏總裝機規模對應的實際發電量其實不足2億千瓦。傳統“風火打捆”方式已經不能滿足新的能效提升要求,風、光及綠氫、甲烷等能源有效整合是未來的趨勢。
而從我國能源消費終端來看,雖然我國電力、熱力和燃氣系統自身能源效率水平已經棲身世界先進水平,但由于不同品類能源所屬系統不同,相關基礎設施和能源數據交互存在壁壘,終端電力、熱力、燃氣等不同供能系統集成互補、梯級利用程度不高,最終導致能源系統整體利用效率較低。快速以園區為突破口開展綜合能源系統建設、推動冷熱電協同互補,是提高全社會用能效率、減低全社會碳排放邊際成本的有效路徑。
另一方面通過完善產業生態鏈、推動產業數字化從而深度提升系統能效。
以我國電動汽車充電站發展為例,我國部分服務區已經開始陸續配套120kW的直流快充樁能夠實現接近超級充電站的充電速度,充電效率已屬于世界前列水平,但中國充電樁的平均使用效率不足5%,這背后凸顯的是電動汽車產業生態化、數字化缺乏導致的另一種系統能效低表現形態。這類系統能效低的問題并非單純技術落后、基礎設施落后可以解決,還需在不斷推進清潔能源汽車占比的同時將充電站、氣站、油站與貨運、客運等平臺以及終端車主的需求信息共享化、平臺化,從而有效提升交通部門整體能源效率,屬于典型的向產業生態要能效和向數字經濟要能效的情景。
從能源設備生產開始
建立全生命周期能效評價體系
隨著可再生能源占比不斷提升,可再生能源因其相對較低的使用成本有望大幅度降低社會用能成本總量,這也使傳統的能源效率概念逐漸失去其度量作用。
一方面從能效對象來看,碳排放相關的能效水平將更受關注。相較于傳統的單位GDP和度電能耗而言,“雙碳”發展目標下能源轉型應該更加關注單位GDP碳排放、人均碳排放和度電碳排放等指標。
另一方面從能效考量周期來看,從能源設備生產開始的碳排放量也應被納入能源效率考量范圍內。
以我國當前的光伏板的生產技術為例,光伏板碳回收周期約為6個月。這一類新能源設備的“生產過程能源消費回收周期”、“生產過程碳排放回收周期”應該與設備生產過程中的碳排放絕對值一同納入未來的能源環境效率評價體系。
在此概念延伸基礎之上,也可以通過使用“生產過程能源消費回收周期”或者“生產過程碳排放回收周期”等概念來補充度量CCS、CCUS等脫碳設備的全生命周期能源效率。
(作者 江海燕 王林鈺)